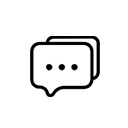明儒罗钦顺在《困知记》中说:“佛法之初入中国,惟以生死轮回之说动人。”因为贪生恶死是人之常情,所以佛教借此来传播。《圆觉经》里说: “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认为普通人总是无法超出恩爱贪欲之外,所以才深陷于轮回之中,只能看到虚幻的世界,只有笃信佛教、修行自我,体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才能躲出六道轮回的痛苦。
张载作为儒者,在《正蒙》中利用哲学来批判了佛教的“涅槃”说,认为它与道教的长生不死都是谬论——
“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
佛老都看到了物质循环的规律,但是他们不是接受这个规律,而是想超出规律之外或者阻挡规律的作用。为了破除他们的幻想,张载根据《周易》提出了系统的物质循环理论。
张载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提出唯物的循环论
物质是不生不灭的
在张载之前,许多思想家把世界的本原称为“太和”、“太极”、“太虚”或“道”,有人说它是无形无象的,也有人说它无形而有理,还有人说它能够生成“气”。对此,张载别树一帜,认为本体的根本特点不是“生气”而是“有气”,气不是从本体中产生出来——或者说气就是本体。他用气来作为构成世界的基质,说世界在本质上就是充满了气的物质世界。
《太和篇》说气分为阴阳两面,浮而上升的阳气为清,沉而下降的阴气为浊。阴性代表气的发散,阴性代表气的凝聚,就如排斥与吸引一样,处于矛盾之中。一元之气本来就存在着,它分为阴阳二性,阳性偏散,阴性偏聚,“阴聚之,阳必散之”,二者虽然对立,但又统一于同一个本体。
天地之气虽然变化多端,难以捉摸,但是有一个基本规律存在于其中,那就是聚散。气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万物,万物瓦解,又将复归于气,这乃是“不得已而然”,“涅槃”和“长生”都违背了这个原则,因而都是虚妄的,它们看不到宇宙物质总量的守恒。
气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万物,万物有形有象,所以才能够被我们所看见、所感知,因此我们称之为“有”;当气分散开,复归无形无象的太虚,就像冰凝释在水中一样,脱离我们的视线与知觉,仿佛退回了黑暗之中,因此我们称之为“无”。如此说来,气其实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所谓的“有”和“无”只不过是我们看见或看不见它而已——也就是说“虚无”是不成立的。
气显现出来,为我们所见,才叫做“有”,“有”的真正意义只是“明”;气隐藏起来,不被我们看见,才称为“无”,故而“无”只是“幽”的不切确说法。
张载说:“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这样他就用《周易》的“幽明”来代替了《老子》的“有无”,证明气是不生不灭的,它只是聚散显隐而已,并没有从无中生成、又消灭回虚无。《横集易说》写道:
“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气聚集在一起,化生万物,有形有象,故为“明”;气分散开来,重回太虚,无形无象,故为“幽”。这便是张载的物质不灭论。
张载的物质不灭论否定老子的“有生于无”和佛教的“寂灭”
用“幽明”来取代“有无”
程颢跟张载一样,都否定“无”,承认“有无”的对立乃是一种误解。他说:
“言有“无”,则多有字;言无“无”,则多无字。有无与动静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闭,可谓静矣;而日月星辰亦自运行而不息,谓之无动可乎?但人不识有无动静尔。”
说有“无”这种状态存在,本身就是一病句,因为“无”如果存在着,那么它就不是“无”了,因为“无”代表的是没有任何东西的空无,所以多了一个“有”字;同样,说没有“无”这种状态存在,也是一个语病,因为“无”就是没有的意思,说无“无”就等于说没有“没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有无的观念乃是一种误解,它把“有”跟“无”视为分离的两端,割裂开来,然后进行单纯的否定。
过去人们也曾把“动”和“静”理解为完全对立的东西,认为静止就是“废然不动”。然而静止其实只是一种相对运动而已,绝对的静止并不存在。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只是绝对运动中的某一种相对平衡状态。
类似的,佛教与道教所理解的虚无、空无也是不存在的,虚无只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一种不为我们所见、所知的存在。所以,真正说来,应用“幽、明”这两个范畴来取代“有、无”,“有”就是“明”,“无”就是“幽”。
张载认为世界不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它的本质也不是空无。世界本来就存在着,只是它最初的状态是分散开的气,故而无形无象,后来气才聚集成为我们现在所能观测到的样子。以后,它可能又会继续分散开,重新复归到无形无象的状态,但那不是“末日”,因为气永远存在。
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无”
张载与王夫之的物质循环理论
气就是物质,气不存在“有无”之分,只是聚散变化而已。气的聚散就是幽明,明和幽就如昼夜一般,区别在于看得见和看不见,而不是存在或不存在。因此气是没有生灭的,不会消灭为无、不会“寂灭”——这是物质不灭论。另一方面,气是运动变化的,遵循聚散的必然规律,气不能只聚而不散,也不能只散而不聚,总是在无穷运动变化中,由聚到散,由散到聚,因而“长生”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物质循环论。
所以张载说:
“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
他用物质不灭论来破除佛教的“寂灭”空虚,认为轮回不可超出;又用物质循环论来反驳道教的“长生”幻想,说有具体的死,但无普遍的亡。这就破灭了宗教唯心主义的创世说和末日说,不给神仙留下任何的空间。
在张载的体系中,运动还不是发展,气的运动是一种聚散往复的循环,而没有进展到上升,因而世界的变化也只是在一个大轮回中旋转。王夫之是张载的信徒,他对这种循环轮回进行更具体的论述,说没有“生灭”,只有屈伸、聚散、幽明。《正蒙注》说:
“车薪之火,一烈已尽,而为焰,为烟,为烬,木者仍归木,水者仍归水,土者仍归土,特希微而人不见尔。”
事物的消灭不是化为虚无,而是进入物质大循环中,继续运动,只是人的眼睛看不到而已。
张载与王夫之
王夫之举了四个物质循环的例子:
一、四季运行,春夏生而秋冬杀,周而复始,是为循环,同时春夏生是旧树发芽,秋冬杀是枝叶枯荣而滋润根本,并非无中生有和消灭无遗;
二、车薪之火,激烈燃烧,化为灰烬,只是发生了转化,而非消灭,这种转化过于希微,人眼看不到而已;
三、凡有形之物都会发生转化,何况不可象者呢?“未尝有辛勤岁月之积,一旦悉化为乌有,明矣。”
四、君子与盗跖不同德性,倘使同灭于无尽,则德性高之人与德性劣等之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德性高之人的血肉之躯虽然转化为其他事物,但其精神、道术、思想、品质仍然永存于后世的观念之中,是为“尧舜周孔之所以万年”。
这些观点虽然都有力地证明了物质不灭和循环的事实,但没有看到上升与下降,有陷入生死轮回、制度永存、人性常在等不变论的危险。 因而受到许多道学家的诘难。
宇宙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
程颐不认同张载的观点,他在入关讲学时,特别批判了物质循环论,说:
“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天地间如洪炉,虽生物销铄亦尽,况既散之气,岂有复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气?……開阖便是‘易’,‘一開一闢谓之变’。”
程颐认为新生的事物并非完全由死灭事物的原质组成,已经散开的气是无法再继续参与造化的,它们不能够再返回本原,不然会造成永动的谬论,它们必定是已经“销铄尽”了。真正的变化并不是往复循环,而是上升发展或下降衰退,所谓“一開一闢谓之变”是也。就好比今天与昨天虽然看上去都是昼夜交替的一天,但每个人的年龄其实都发生了变化。
程颐用发展观来改造张载的循环论,但这样他又得承认“生气”不是“气本”了,气如果是由某个本体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那么它就存在生灭。程颐提出了一个“真元”本体,用它来“生气”,说:
“真元之气,气所由生。”
“真元自能生气。”
“人之气生于真元,天之气,亦自然生生不穷。”
程颐用发展观来对张载的循环论
在朱熹的体系里,我们发现程颐的观点其实就是“理生气”的雏形。朱熹也不认可张载的物质循环论,他说:
“横渠辟释氏轮回之说。然其说聚散屈伸处,其弊却是大轮回。盖释氏是个个各自轮回,横渠是一发和了,依旧一大轮回。”
佛教是每个人各自的轮回,张载为了避免这种观点,反而建立起了一个全宇宙的大轮回,仍未克服佛教。因此,程朱放弃“气本论”,主张“理本论”,用“理”来生出“气”。
到了明朝时,罗钦顺发现张载的“气本论”与程朱的“理本论”都有将“理”和“气”分为两物的倾向,他说:
“张子《正蒙》‘由太虚有天之名’数语,亦是将理气看作二物。”
“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决是二物’。”
正因为张载与程朱都把“理”和“气”视为二物,才导致了“大轮回”与“生气”两种不可弥补的缺陷。
张载主张物质不灭以避免“生气”的创世说,却掉入“大轮回”之中;程朱主张“气”生于“理”来弥补轮回的缺陷,但又坠入创世说里。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
对此,罗钦顺提出了“理”和“气”统一的思想,认为它们并非“二物”,气是本体,理是气的属性——是气之条理性。用“理一分殊”的思想来说,从普遍的、共性的即“理一”的角度看,物质是不会寂灭成为空无一物的虚空状态,世间存在的物质总量永远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从特殊的、个性的即“分殊”的角度看,具体的、个别的物质是会发生生死的循环,会从一种状态质变为另一种状态。
通过对罗钦顺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我们认为世界的运动轨迹并不是一个从起点开始又回到起点的封闭圆圈,而是一个不断回到起点又不断超出起点的螺旋。是一种类似于双螺旋的推进过程。一般的物质是没有生灭的,客观存在的东西永久存在,但具体的物质是有生有灭的过程,当然这里的生灭是相对的的,指其质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