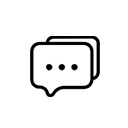關於老官山出土文獻的研究,從已經發表的老官山出土醫簡的研究論文和專書來看,分歧最大的在於醫簡的命名,成都中醫藥大學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成的整理小組(以下簡稱“整理小組”)擬定的命名方案與之前公佈的書名已有較大的不同, 或許釋文正式發表時還會再變。
筆者依據竹簡的規格、編纂體例和內容將老官山出土醫簡分為5種:《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脈書》《針方》《六十病方》《醫馬書》。
在老官山出土醫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簡是編號361–628簡,差不多占了全部出土醫簡數量的40%。 這部分竹簡出土時已經散亂堆放在一起,從結構上看,簡的長度皆為35.7 cm、寬0.9 cm、厚0.1 cm,字迹一致,體例也相同; 從內容上看,涉及病候、經脈、別脈、診脈法,與張家山出土漢簡《脈書》的基本構成相同,而且二者的書寫體例也完全相同——簡頭皆標有圓點符“”,甚至連竹簡的規格也十分接近——長度僅相差1 cm; 從內容上看,將老官山“十二脈”文字與張家山《脈書》逐條逐字比對後發現,後者獨有的特徵性文字,包括錯別字,大量見於老官山“十二脈”文字中。 綜上可判斷:老官山出土漢簡361–628簡皆出自同一部書,書名可題作“老官山《脈書》”。
面對眾多的命名方案,為避免新的混亂,本文儘量直接按其內容引錄竹簡釋文,例如“十二脈”“別脈”“診脈”等。
以下重點考察老官山《脈書》中的“十二脈”“別脈”和“診脈法”文字。 另有少量論述經脈、別脈循行、病候,以及相關診脈法的零散醫簡被編入361–628簡之外的醫簡中,本文也附帶考察。
本文所引老官山《脈書》竹簡釋文主要依據《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1〕,凡該書釋文附有圖版者,皆一一核對,原釋文辨識錯誤或斷句有誤者,以按語形式說明。 凡釋文標注有竹簡編號者皆一一注明,以便於讀者核查。 為减少造字數量,除老官山漢簡之外的出土文獻,凡釋文標注有正體字者直接引用正體釋文。
1十二脈
“十二脈”共計35枚竹簡,出土發掘時編聯已斷,次序錯亂,整理小組確定的次序為:手大(太)陽脈、手陽明脈、手少陽脈、辟(臂)大(太)陰脈、辟(臂)少陰脈、心主之脈、足大(太)陽脈、足少陽脈、足陽明脈、足大(太)陰脈、足少陰脈、蹶陰脈。
據筆者考察,“十二脈”的底本採用的是張家山漢簡《脈書》本《陰陽十一脈灸經》(即“丙本”,以下簡稱“陰陽十一脈”)和《足臂十一脈灸經》(以下簡稱“足臂十一脈”),抄錄管道為合抄改編。 故以下的文獻比對主要集中在老官山“十二脈”、《足臂十一脈》、《陰陽十一脈》(丙本)三者之間。
十二脈”的體例:第一,關於脈之起點,現已公開的9條脈起點皆用“系”字,而止點有心主之脈、足太陽脈、足少陽脈、足太陰脈、厥陰脈5脈也作“系”,明顯看出統一以“系”字作為十二脈起止點規範術語的用意; 第二,十二脈病候具體病症的總結與《陰陽十一脈》(丙本)更為接近,但不再以“是動則病”和“其所產病”分類,除手太陽脈作“所生病”外,其餘十一脈病候前皆冠以“其病”二字,與《足臂十一脈》格式相同; 第三,十二脈的循行方向,依《足臂十一脈》,皆自下而上向心性循行; 第四,十二脈的命名:手三陰脈起點皆起於掌中,尚未延伸至相應的手指,故手三陰脈仍以“臂”+“三陰”命名作“臂太陰脈”“臂少陰脈”“心主之脈”。 其中,“心主之脈”的命名採用了《陰陽十一脈》(丙本)的格式,即於“脈”之前加一“之”字,而其餘十一脈的命名皆未用“之”字。
以下就已經公開部分釋文的手太陽脈、手陽明脈、臂太陰脈、臂少陰脈、心主之脈、足太陽脈、足少陽脈、足太陰脈、足少陰脈、厥陰脈,作具體分析。
1.1手太陽脈
“十二脈”記述手太陽脈的竹簡共有2枚,即第448(?)簡,和第471殘簡,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臂泰陽脈:出小指,循骨下廉,出臑下廉,出肩外廉,出項□□□目外眥。 其病:臂外廉痛〔2〕6。 (《足臂十一脈》)
·肩脈:起於耳後,下肩,出肘內廉,出臂外腕上,乘手背。 是動則病:領種痛,不可以顧,肩似脫,臑似折,是肩脈主治。 其所產病:領痛,踝,肩痛,肘外痛,為四病〔3〕120-121。 (《陰陽十一脈》丙本)
簡448(?):·手大(太)陽脈,毄(系)小指,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廉,出腝下廉,上肩,循頸出耳後,屬目外貲(眦)湄,所主病:領穜(腫),痛矦(喉)〔4〕64/簡471(殘簡):貞痛,脥痛,肩□,腝痛,肘痛,頸痛,辟(臂)外痛,手背痛〔1〕228。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關於手太陽脈循行與病候,需要討論的有以下6點:
第一,《陰陽十一脈》(丙本)肩脈循行“出肘內廉”,其中“肘內廉”系陰脈循行分野,陽脈不當行於此,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甲本作“出臑外廉”、乙本為“出□外廉”,而老官山手太陽脈循行作“出肘內廉”,獨與丙本同。 又據《陰陽十一脈》丙本,老官山病候釋文斷句應作“領穜(腫)痛,矦(喉)……”; “肩□”,在丙本作“肩痛”,甲本缺,乙本作“臂痛”,則老官山文字此病症亦當錄自丙本。 從現時已經公開的“十二脈”釋文來看,引用《陰陽十一脈》之文,凡甲、乙、丙3本不同者,也皆獨與丙本相合。 可知,老官山“十二脈”文字編者所依據的《陰陽十一脈》底本系“丙本”,即張家山漢簡《脈書》傳本。
第二,“手太陽脈”竹簡的編號,整理小組標注為“448471(殘斷)”,而所附圖版下標注的卻是“478、471”,二者不相合。 雖知471簡為殘簡,但不詳簡頭還是簡尾殘缺,即不詳簡471與簡448能否首尾相接。 如果首尾相接,據《陰陽十一脈》(丙本),簡448最末一字“矦”下應作“踝”(“”字之誤。乙本作“矦淠”無誤),而現時下接圖版文字為“貞痛”,與“喉”字相接則作“喉貞痛”,此或因抄者改編,或“矦”下有脫簡。
第三,“屬目外貲(眦)湄,所主病”句,經核查圖版確認此處釋文、斷句應作“屬目外貲(眦)。治所生病”。 整理小組將“治”誤釋為“湄”,“生”誤釋作“主”,並將屬下讀的“治”字誤接於上。 有意思的是,“治所生病”這一特別的表達也是因為“十二脈”編者對原文本的斷句失誤造成的。 《陰陽十一脈》(丙本)原文為“是肩脈主治其所產病……”,正確的斷句為“是肩脈主治。其所產病……”,碰巧的是,“治其所產病”在《陰陽十一脈》(丙本)恰好被抄在簡頭,老官山“十二脈”編者未加詳考將屬上讀的“治”字誤屬下而抄作“治所生病” 。 而正是這一不該有的失誤將編者的更大失誤暴露在陽光下:關於病候,老官山“十二脈”明確從《陰陽十一脈》“是動則病”項下輯錄病症,但卻沒有採用原書的“是動則病”“其所產病”的病候分類。 問題是“其所產病”是與“是動則病”對舉而言的,既已删去“是動病”,單言“所生病”顯得很突兀,抄者也很快意識到這個問題,故在其他十一脈病候前統一改成了“其病”二字。 而手太陽脈病候“治所生病”中所誤抄的“治”字恰好留下了其從《陰陽十一脈》改編的鐵證。 由此可做出這樣一個推斷:老官山“十二脈”有可能是始於“手太陽脈”,儘管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這都不是一個常見的十二脈的編次。 而從這一連串的失誤,以及接下來的更多的失誤中,讓人產生這樣的印象:“十二脈”編者不像是扁鵲醫學的傳人。 因為從倉公醫案所引厥陰脈、陽明脈病候看,“是動則病”是其所受之扁鵲《脈書》經脈病候的表述特徵。 如果老官山“十二脈”編者是扁鵲醫學的傳人,不可能不知自家經典的特徵,也不大可能出現“治所生病”這樣的低級失誤。
第四,又有052殘簡作“□□所米病:目外顏暨□□後臂臑後廉循半出中指□下”〔1〕257,其中“所米病”亦當是“所生病”,未詳原文確作“所米病”,還是釋文有誤,待圖版公開後再詳考。 從“產”到“生”的一字之改,可以讀出抄本的時代資訊。 田煒〔5〕在系統比較了出土秦和西漢早期文獻中“生”和“產”的用例後指出:“產”的流行反映的是秦人的用語習慣,秦代用政令的管道把秦人的用語習慣固定下來,推廣到其他地區,並且限制“生”的使用,“產”囙此承擔了“生”的功能,至西漢早期“生” 又重新流行。 可見,老官山出土文獻的這兩處“所生病”不僅成為傳世經脈文獻“所生病”的最早出處,而且為老官山脈書簡的抄寫年代確定提供了一個文字學的證據。
第五,關於手太陽脈從頸部至止點“目外眥”的循行路徑有2種:已知出土的漢以前文獻皆從“耳後”行至目外眥,老官山出土針灸木人同樣如此; 傳世文獻《靈樞·經筋》手太陽之筋也從“耳後”至目外眥,而《靈樞》“經別”“營氣”“經脈”3篇皆採用了從頸部經“耳前”到目外眥的循行路徑。 既然手太陽脈採用了“三陰三陽”命名法,那麼其循行路徑就須遵循“人體三陰三陽分部法則”〔6〕173-176,顯然出土文獻、《靈樞·經筋》,以及針灸木人手太陽脈從頸部經“耳後”至目外眥的循行路線符合“人體三陰三陽分部法則”。 關於手太陽脈從頸到目外眥這一段循行路線的複雜演變過程的考察,詳見筆者《經脈理論還原與重構大綱》第8章和第13章〔6〕。
第六,老官山手太陽脈文字有一個明顯的改動,將此條脈的名稱由原文本的“臂泰陽脈”改作“手大陽脈”,手三陽脈的其餘兩條脈也相應改作“手少陽脈”“手陽明脈”。 因為早在《足臂十一脈》手三陽脈的起點已經延伸至相應的手指部,再加上有足脈命名的參照,這一改動應當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
1.2手陽明脈
“十二脈”記述手陽明脈的竹簡共有2枚,現時公開的是簡472釋文,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臂陽明脈:出中指間,循骨上廉,出臑□□上,凑枕,之口。 其病:病齒〔痛〕,□□□□〔2〕6。 (《足臂十一脈》)
·齒脈:起於次指與大指上,出臂上廉,入肘中,乘臑,穿頰,入齒中,夾鼻。 是動則病:齒痛,朏腫,是齒脈主治。 其所產病:齒痛,朏腫,目黃,口幹,臑痛,為五病。 及□〔3〕121。 (《陰陽十一脈》丙本)
簡472:·手陽明脈,毄(系)次指與大指之上,出辟(臂)上廉,入肘中,乘腝,出肩前廉,循頸穿頰,入口中。 其病:齒齲痛口,辟(臂)朏(屈)穜(腫)〔4〕64(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關於手陽明脈循行與病候,需要討論的有以下3點:
第一,循行較《陰陽十一脈》多出“出肩前廉,循頸”6字,不見於漢以前出土文獻,而在《靈樞·經脈》可見對應的描述“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頸”〔7〕31。
第二,關於病候“齒齲痛口,辟(臂)朏(屈)穜(腫)”,釋文、斷句皆有誤,正確的釋文、斷句為:“齒齲痛,口辟(僻),朏(䪼)穜(腫)”。 《陰陽十一脈》丙本於“所產病”五病後另有新增病候“及□”,故“口辟”症很可能也抄自丙本新增之病症。
第三,另有簡112作“□陽明□起手大指與次指上,循臂”〔1〕257,文字與《靈樞·經脈》更接近。 未詳與“十二脈”皆出自相同原本的不同抄本,還是出自不同的本子,有待完整釋文公開後再詳考。
1.3臂太陰脈
“十二脈”記述臂太陰脈的竹簡共2枚,現已公開的釋文系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臂泰陰脈:循筋上廉,以凑臑內,出腋內廉,之心〔2〕6。 (《足臂十一脈》)
臂钜陰脈:在於手掌中,出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內陰,入心中〕〔2〕12。 (《陰陽十一脈》甲本)
臂巨陰之脈:在於手掌中,出臂內陰兩骨之間,上骨□□□□□□〔陰,入心中〕〔3〕123。 (《陰陽十一脈》丙本)
辟(臂)大陰脈,毄(系)手掌中,循辟(臂)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辟(臂)內陰,至亦(腋),入心〔8〕13。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關於臂太陰脈循行,有一處不當的改編,《陰陽十一脈》(丙本)原文作“出臂內陰兩骨之間”,這裡的“出”字表示脈口處,改作“循”字,欠妥。 另在足少陽脈、足太陰脈也見有類似的改編,說明抄者已不詳原本“出”字的特殊含義。 而且從“循臂內陰兩骨之間”這一特徵性的文字來看,老官山文字引用的《陰陽十一脈》,採用的依然是丙本,甲本、乙本作“出內陰兩骨之間”。
1.4臂少陰脈
“十二脈”記述臂少陰脈的竹簡共2枚,現已公開的釋文系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臂少陰脈:循筋下廉,出臑內下廉,出腋,凑脅〔2〕6。 (《足臂十一脈》)
臂少陰之脈:起於臂兩骨之間,之下骨上廉,筋之下,出臑內陰,入心中〔3〕123。 (《陰陽十一脈》丙本)
辟(臂)少陰脈,毄(系)掌中,循辟(臂)內陰兩骨之間,下骨上廉,筋之下,以上入肘內廉,出腝內陰,下出亦(腋)下,入心中〔8〕18。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關於臂少陰脈循行與病候,需要說明的是,老官山“十二脈”循行方向皆自下而上向心性循行,則手少陰脈從“腝內陰”至“腋”是上行,循行文字作“下出腋下”,有點費解。 從“心主之脈”的循行來看,其明顯是從腋下脅入心。 故這裡“臂少陰脈”若作“下出腋下,入心中”,則與心主之脈重,非是。 之所以出現此誤,是因為臂少陰脈與心主之脈混淆由來已久,混淆的主要原因在於對“心主”一詞的不同解讀。 在早期扁鵲醫學中,“心主”乃“心為五臟六腑之主”之義,心主之脈乃真心之脈,故早期與心相關的心之原、心脈之五輸; 背俞、腹募皆與心主脈關聯。 從《足臂十一脈》所載之“臂少陰脈”來看,不論是循行還是病候皆與心無涉,而在《陰陽十一脈》乙本、丙本,臂少陰脈循行文字已明言“入心中”,病候主“心痛”,由此拉開了臂少陰脈、心主之脈從相混到逆轉的序幕。 而《靈樞·邪客》“包絡者,心主之脈也”〔7〕128、《靈樞·經水》“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7〕42之說,則標示著臂少陰脈、心主之脈與心關係的逆轉。 然而逆轉後的新說被接受卻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歲月,直到唐代王冰注《素問》時,仍為此二脈相混之狀所困:
心少陰脈,支別者,循胸出脅。 手心主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其支別者,亦循胸出脅〔9〕146。 (《素問·髒氣法時論》王冰注)
心少陰脈,循胸出脅,故俞在焉〔9〕23。 (《素問·金匱真言》王冰注)
王冰在不同的篇皆將《靈樞·經脈》屬於手心主厥陰之脈的循行文字“循胸出脅”作為心少陰脈循行引用,特別是第一條注文手少陰脈與手心主脈同時引錄,很難用傳抄之誤來解釋。 再聯系到《足臂十一脈》所載之臂少陰脈循行也明言“凑脅”,足見此二脈混淆由來已久。
1.5心主之脈
“十二脈”記述心主之脈的竹簡1枚,現時只公開了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臂少陰脈:循筋下廉,出臑內下廉,出腋,凑脅〔2〕6。 (《足臂十一脈》)
心主之脈,毄(系)掌中,上出辟(臂)中,出紂(肘)中,走亦(腋)下,□□,入匈(胸),循匈(胸)裏,上加大陰,上循□嚨,下毄(系)心〔8〕14。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關於心主之脈,值得一提的有兩點:
第一,老官山出土漢簡“十二脈”中的心主之脈循行明顯受到《足臂十一脈》中“臂少陰脈”的影響,文字中出現了“走亦(腋)下”這一點,其後所缺二字,當作“奏脅”,或至少有一“脅”字。 這從其後的循行路線也可推知,既曰“循(胸)裏,上加大陰”,則必定是從腋下脅,入胸,而不可能像手太陰脈那樣從腋直接橫向入胸。
第二,老官山出土漢簡心主之脈與心的關聯更直接、更緊密——系心,在《靈樞》中歸屬於手少陰脈的特徵性循行文字皆見於此“心主之脈”,例如“上循□嚨”,在《靈樞·經脈》作“上挾咽”,《經別》篇作“上走喉嚨”,皆為手少陰脈循行。
1.6足太陽脈
“十二脈”記述足太陽脈的竹簡有3枚,全部釋文已公開,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足泰陽脈:出外踝婁中,上貫腨,出於郤; 枝之下; 其直者貫□,夾脊,□□,上於脰; 枝顏下,之耳; 其直者貫目內眦,之鼻。 其病:病足小指廢,腨痛,郤攣,脽痛,產痔,腰痛,夾脊痛,□痛,項痛,手痛,顏寒,產聾,目痛,鼽衄,數癲疾〔2〕3。 (《足臂十一脈》)
钜陽之脈:於踵外踝中,出中,上穿臀,出厭中,夾脊,出於項,上頭角,下顏,夾頞,目內廉。 是動則病:沖頭痛,目似脫,項似伐,胸痛,腰似折,髀不可以運,胠如結,腨如裂,此為踵蹶,是钜陽之脈主治。 其所之病:頭痛,耳聾,項痛,灊强,瘧,背痛,腰痛,尻痛,痔,胠痛,腨痛,足小指痹,為十二病〔3〕118-119。 (《陰陽十一脈》丙本)
足大(太)陽脈,(系)足小指循足胕外廉,出外果(踝)後脛中,循〔腨〕而上,出〔胠〕中以上,其支者入州,直者貫尻夾脊,以上出項,上頭角,夾頎,下顏頞,(系)目內眦。 其病:□□,顏痛,訅衄,頭痛,北(背)痛,夾脊痛,脊强,要(腰)痛,尻腗(脾)痛,痔,州痛,胠痛,腨痛,踵與果(踝)痛,足小指畀(痹)。 癲狂,回目,目莫如毋見,□目,□踵,頭瘧風〔1〕236。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需要討論有以下4點:
第一,《足臂十一脈》原文“枝之下”中之“”字,不見於字書,也不見於其他出土文獻,參照《陰陽十一脈》的循行及相關病候,此“”當系“腗(髀)”之俗訛。 髀在尻之外側,《素問·骨空》曰:“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9〕324。 楊上善注曰:“髀樞,謂髀骨、尻骨抵相入轉動處也”〔10〕。 關於足太陽脈與髀的關聯,不僅在《足臂十一脈》這一分支中體現,老官山出土針灸木人足少陽脈也從髀樞處發出一分支至足太陽脈; 在傳世文獻也明確見於《靈樞·經脈》,特別是《靈樞·經筋》還記述了足太陽與足少陽合於髀樞的臨床依據。 《陰陽十一脈》在綜合《足臂十一脈》這一分支時更是明確作“出厭中”(髀樞)。 《黃帝明堂經》載足太陽“委中”主治曰“髀樞痛,外引季脅,內控八窌”〔11〕234。 足見足太陽脈合於髀樞有充分的文獻、理論和臨床依據。 而老官山“十二脈”編者將“”字改作“州”,並在病候中新增“州痛”之症,以與改編後的循行路線相呼應。 然而又較之《足臂十一脈》《陰陽十一脈》更強調了“髀”部的病候——“尻腗(脾)痛”之症,既然已經將《足臂十一脈》去“脾”的分支改作“其支者入州”,這裡卻特別強調“脾痛”之症,難以自圓。 假定老官山“十二脈”編者對於原本《足臂十一脈》原文“”理解無誤,同時又想強調足太陽脈與肛門的聯系,完全可以作如下處理:“足大(太)陽脈……出〔胠〕中以上,其支者至脾(髀),其直者入州,還出貫尻夾脊……”
第二,足太陽脈在頭面部的循行,《足臂十一脈》仍採用主幹與分支的管道表達作“上於脰;枝顏下,之耳;其直者貫目內眦,之鼻”,而《陰陽十一脈》採用“變向折返”的一線連接管道作“上頭角,下顏,夾頞,系目內廉”,是說從頭下顏之後,再折返向上 “夾頞,至目內眦”,老官山本“十二脈”編者這時沒有像之前採用《足臂十一脈》的表述管道,而是採用了《陰陽十一脈》“變向折返”的一條線連接管道作“上頭角,夾頎,下顏頞,(系)目內眦”,此處較原本多“頎”字,而“頞”前脫一“夾” 字,遂使語義不通。順便說,從這個實例中也可看出,老官山“十二脈”所採用的《陰陽十一脈》底本系丙本,因為甲本、乙本“頞”字皆寫作“”。
第三,病候最後作“足小指痹。癲狂,回目,目莫如毋見,□目,□踵,頭瘧風”。其中“足小指痹”是《陰陽十一脈》“所產病”的最後一症,此後的病症應是改編者新增病症,看得出該編者此處也有模仿《脈書》本《陰陽十一脈》的體例的意思,《脈書》本 “所產病”病症之末皆有病症數的統計,新增病候之前皆冠有一“及”字,與原有病候不相混,顯得體例非常嚴謹、合理。而老官山文字改編,不僅體例不及《脈書》嚴謹,而且所增病症也有失誤,具體到這一例,所添加的病症中,“癲狂”已見於《足臂十一脈》 ,不應置於新增病候中;“回目”,《千金要方·扁鵲華佗察聲色要訣第十》卷二十八作“目回回直視”,系扁鵲診生死候中的“死症”;在張家山《脈書》中作“目環視雕”,亦為五死症之一;在《脈經·診五髒六腑氣絕證候第三》又作為“心絕” 之候,皆不涉及足太陽脈。“目莫如毋見”症,則見於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及張家山《脈書》足少陰脈病候作“目瞙如毋見”。總之,這幾條添加的病候疑點較大,恐有誤。
第四,關於足太陽脈循行,另有一殘簡050作“□□□足小□外廉,循外踝後,以上外”〔1〕257,雖與新編之“十二脈”文字相近,但並不相同,待全部釋文公開後再詳考。
1.7足少陽脈
“十二脈”記述足少陽脈的竹簡共有4枚,現只公開了第598簡,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足少陽脈:出於踝前,枝於骨間,上貫膝外廉,出於股外廉,出脅;枝之肩髆;其直者貫腋,出於項、耳,出枕,出目外眥。其病:病足小指次指廢:胻外廉痛,胻寒,膝外廉痛,股外廉痛,髀外廉痛,脅痛,□痛,產馬,缺盆痛,瘺,聾,枕痛,耳前痛,目外眥 痛,脅外腫〔2〕3。(《足臂十一脈》)
少陽之脈:系於外踝之前廉,上出魚股之外,出脅上,出耳前。是動則病:心與脅痛,不可以反,甚則無膏,足外反,此為陽〔蹶,是少陽脈主治。其所產病〕:□□痛,□痛,項痛,脅痛,瘧,汗出,節盡痛,髀廉痛,□痛,魚股痛,厀外廉痛,振寒,足中指痹 ,為十二病。及溫〔3〕119。(《陰陽十一脈》丙本)
598簡:夜(腋),循□而上耳前,系目外眥。其病:足小指之次指痛,足胕上廉痛,外果(踝)前痛,脛外廉痛,厀(膝)魚股外廉痛,畀痛,脅〔1〕283-284。(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需要討論的有以下4點:
第一,從同墓出土的針灸木人足少陽脈循行來看,文字“循□而上耳前”中的缺字可補作“頸”字,《靈樞·經脈》也作“頸”。
第二,“上耳前”,《陰陽十一脈》丙本作“出耳前”,這裡的“出”字有特殊含義,改作“上”字欠妥。又,“耳前”,甲本、乙本皆作“現時”。
第三,足少陽脈從腋脅至止點“目外眥”存在兩種不同的循行路徑:其一,耳後:《足臂十一脈》《靈樞·經筋》;其二,耳前:《陰陽十一脈》、老官山“十二脈”、《靈樞·經別》;《靈樞·經脈》主幹選擇的是“耳後”路徑,又通過分支的形式而兼具了“耳前” 路徑。如果足少陽脈從頸至目外眥這一段循行只是表達“頸”與“目外眥”這兩點的關聯,那麼這兩種不同的路徑表達的意義是相同的。選擇哪一種方案關鍵要看“從頸至目外眥”之間是否還有其他的點,以及這些點是在耳前還是耳後。選擇“耳前” 路徑者,其標脈只有一點在目外眥,故遵循“兩點間最短路徑”的原則,直接從脅循側面部至目;而選擇“耳後”路徑者,其標脈除了“目外眥”這一點外,還於耳後、側頭部發現更多的標脈點,要串連所有這些點就必須經“耳後”而行。
第四,另有殘簡114曰:“少陽脈□小指之次循外踝前廉上循”〔1〕257,其與“十二脈”的關係,有待全部釋文公開後詳考。
1.8足太陰脈
“十二脈”記述足太陰脈的竹簡共有4枚,現已公開的釋文只是關於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足泰陰脈:出大指內廉骨際,出內踝上廉,循胻內〔廉〕,□膝內廉,出股內廉〔2〕5。(《足臂十一脈》)
太陰之脈:是胃脈也。被胃,下出魚股之陰下廉,腨上廉,出內踝之上廉〔3〕121。(《陰陽十一脈》丙本)
足大陰脈,(系)大指,循足(胕)內廉,〔出內〕果(踝)□廉,循骭骨內廉,出膝內廉,〔循股〕內廉,而上入腹〔屬〕腸胃,系〔咽〕〔8〕21。(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需要說明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循股〕內廉”,應據《足臂十一脈》作“出股內廉”,不詳整理小組據何補“循股”二字。
第二,“系咽”不見於所有出土文獻,同墓出土的針灸木人也沒有類似的循行,不詳整理小組據何補“咽”字。
1.9足少陰脈
“十二脈”記述足少陰脈的竹簡共有3枚,皆有殘斷,現已公開的釋文系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足少陰脈:出內踝婁中,上貫腨,入郤,出股,入腹,循脊內□廉,出肝,入胠,系舌□〔2〕4。 (《足臂十一脈》)
少陰之脈:系於內踝之外廉,穿腨,出郤中央,上穿脊之內廉,系於腎,夾舌本〔3〕122。 (《陰陽十一脈》丙本)
足少陰脈,(系)□□,出內果後脛□循□□□內廉,穿陰股而上,夾脊內廉,〔系於腎〕,上夾舌本〔8〕27。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有一明顯的改編失誤,《足臂十一脈》原文作“出股,入腹,循脊內□廉”,明確為體內循行線; 《陰陽十一脈》作“上穿脊之內廉”,雖不甚明確,但也不至於誤解,而老官山文字改作“穿陰股而上,夾脊內廉”,容易誤解為體表循行線,與足太陽脈腰骶部循行“貫尻夾脊”相混。
1.10厥陰脈
“十二脈”記述足厥陰脈的竹簡共有5枚,其中有2枚殘斷,現已公開的釋文只是關於該脈的循行文字,相關文字的對照如下:
足厥陰脈:循大指間,以上出胻內廉,上八寸,交太陰脈,□股內,上入脞間〔2〕5。 (《足臂十一脈》)厥陰脈:系於足大指叢毛之上,乘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五寸而出太陰之後,上出魚股內廉,觸少腹,大漬(眦)旁〔2〕11。 (《陰陽十一脈》甲本)
厥陰之脈:系於足大指叢毛之上,乘足跗上廉,去內□□□□□□□□□□□□□□□□□□□,觸少腹,夾旁〔3〕122。 (《陰陽十一脈》丙本)
〔足〕蹷(厥)陰脈,系足大〔指叢〕毛上,乘〔足胕〕上廉,〔去內〕果一寸,循脛內廉,上果〔五寸〕,交大陰脈,□□腹,夾佩,以上(系)齊(臍)〔8〕24。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需要討論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此時尚未出現“手厥陰”的脈名,“厥陰”特指足脈,故此處脈名“厥陰脈”前不當補“足”字。 《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未加“足”字,是。
第二,關於厥陰脈的止點,《陰陽十一脈》甲本的釋文作“大漬”,丙本作“夾”,今老官山漢簡厥陰脈作“夾佩”,可證張家山出土《脈書》釋文“夾”是。 《說文解字》曰:“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段注曰:
鄭注《禮》曰:古者佃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12〕362。
“”即“巿”之後起字,其本義是指上古用於遮蔽前陰部的原始服飾,後文明社會又以布帛為資料製成各類佩飾綴於衣前以仿古義,謂之“佩”。 可知,老官山“夾佩”與《脈書》“夾”字异而義同,原為古人“蔽前”(遮蔽前陰)之飾,這裡用作“夾前陰”之委婉語。 正因為厥陰脈止於前陰部,故張家山《脈書》所述厥陰脈病候突出了前陰病症,又《靈樞·經脈》所載之足厥陰之別的止點為“上睾,結於莖”,病候悉為前陰病症; 老官山出土的針灸木人厥陰之脈也止於前陰部。 馬王堆出土帛書《陰陽十一脈》甲本圖版經筆者仔細覆核實為“夾幘”二字,而釋文作“大漬(眦)”,非也。
2間別之脈
“間”與“別”皆有“分離”“分別”之義。 別者,另也,常與“正”相對舉,故有“正脈”(經脈)、“別脈”之稱; “間”謂“零散”,故有“散俞”“間穴”之稱。 老官山《脈書》以“十二脈”為“經脈”(即“常脈”“正脈”之義),而以“十二脈”之外的所有脈為“間別”之脈。 可知,老官山《脈書》不僅是關於“十二脈”的最早文字,同時也是關於“聯系之脈”的最早分類,而此分類被傳世文獻《靈樞·經脈》傳承,只是改用單字“別”表達“間別”之義。
從已經公開的老官山《脈書》釋文看,可以確定為“別脈”者有兩篇,其中一篇約200字,記有9條別脈的名稱、循行、病症和灸療,即“間別賛(贊)脈、間別月(肉)理脈、間別齒脈、間別□□、間別辟(臂)陰脈、間別辟(臂)陽脈、間別大(太) 陰脈、間別少陰脈、間別大(太)陽脈”9條別脈。 所記9條別脈皆一脈一簡,文字簡略,體例相同:脈名前皆冠有“間別”二字; 脈之起處曰“出”,止處曰“凑”; 循行路徑多是“起”“止”間的兩點一線; 主病也極簡,多為一二病症,病症多為痛症,並與循行部位相應,即痛症部位與循行部位呈“點對點”對應關係; 別脈治療方法均是灸該脈所“出”之處——即脈之俞。
另一篇記述“足大陽脈”“足陽明脈”“間□足大陰”3條別脈,文字同樣很簡略,記述脈的名稱、循行、病候。 與前節9條別脈有兩點不同,其一,沒有提及病症的針灸治療; 其二,“足大陽脈”“間□足大陰”脈名雖與前一篇重名,但內容及體例皆不同。
可以看出,與“十二脈”不同的是,“別脈”文字只是從原文本輯錄,未加改編,名稱、體例都一仍其舊。 別脈不同的命名管道,以及不同的編纂體例正是其出自不同時期不同文字的證據。
由於老官山出土醫簡現時只公開了一部分,“別脈”的確切數位還無法確定,可能還有一些屬於“別脈”的竹簡混雜在尚未公開的醫簡中。 以下僅就已公開釋文的臂陰脈、足太陰脈、足太陽脈加以考察。
2.1臂陰脈之別
·間別臂陰脈,出脥,凑心。 脥痛,心痛,久(灸)臂陰〔1〕238。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說文解字注》曰:“夾,持也。從大,夾二人。段玉裁注曰:夾,各本作俠”〔12〕492。 《集韻》曰:“胠,腋下也。或從劫,亦作脥”〔13〕。 是以夾持之處為“脥”。
從“間別臂陰脈”病候下的灸方可知此脈原名“臂陰脈”(“間別”二字是後加的),此脈“出脥,凑心”。 “脈之所出”曰“脈口”(言診脈部位)、“脈俞”(言治療部位),此脈口、脈俞所以能治遠隔之處“心”的病痛,是因為二者之間有脈的聯系,故於診療點“脥”與所診療部位“心”之間以一脈相連。 此脈即以脈之所“出”之處為起點; 以脈口、脈俞所診療之遠隔處為止點; 以起、止處的痛症為“病候”,治療則取脈之所“出”的脈俞“臂陰”,而此“臂陰”同時也用作連接“脥”與“心”整條脈的名稱。 這便是古人建立此脈以及其他脈的經驗基礎和理論邏輯。
正如段玉裁所言,“夾”字在古醫籍中多寫作“俠”字,如穴名“俠白”即是:
俠白,在天府下,去肘五寸動脈,手太陰別。 刺入四分,灸五壯。 主心痛,咳,幹嘔煩滿〔11〕141。 (《黃帝明堂經》)
臂太陰脈:循筋上廉,以奏臑內,出腋內廉,之心。
其病:心痛,心煩而噫。 諸病此物者,皆久(灸)臂太陰脈〔2〕6。 (《足臂十一脈》)
這兩條文字,特別是《黃帝明堂經》所述脈之循行及病候與前述“臂陰脈”極相近,而脈名一作“手太陰別”,一作“臂太陰脈”,老官山漢簡則作“間別臂陰脈”。 儘管“間別”“別脈”的分類是在“經脈”的概念誕生之後出現的,而就以上3條文獻而言,被歸屬於“別脈”類的“臂陰脈”和“手太陰”反映的卻是“臂太陰脈”成型之前的早期形態。 如果單從文字看,《足臂十一脈》所載之“臂太陰脈”較之於“間別臂陰脈”,實質性的差异似乎只是循行路線在手腕處(相當於太淵脈處)多出一點,然而這“一點”之差卻形成二者間的天壤之別,成為古人構建經脈學說思路突破的“轉捩點”,討論詳見下文 “討論”部分。
從“臂陰脈”這一脈名來看,“經脈”(“十一脈”“十二脈”)的命名在採用“三陰三陽”命名法之前,曾有一個應用“一陰一陽”“二陰二陽”命名法的過渡階段。在老官山出土漢簡9條“間別”脈中,下肢脈的名稱已見有“太陰”“少陰”“太陽”這樣 “二陰二陽”命名的特徵,而上肢脈採用陰陽命名法的只有“臂陰”“臂陽”,還處於“一陰一陽”命名法的階段。而且這種以“一陰一陽”命名的脈還明確見於更早期的出土文獻:“五,一曰啟兩臂陰脈。此治□□方”〔14〕(《裏耶秦簡〔壹〕》)。 “三陰三陽”的經脈命名,很可能是先從足脈開始,而後再類推到手脈,“手厥陰”之名很晚出現,因而直到老官山“十二脈”文字,足厥陰脈仍只作“厥陰脈”,脈名不加“足”字。
從《黃帝明堂經》將“間別臂陰脈”的文字直接歸屬於“手太陰別”來看,手三陰脈最先確立的是“臂太陰脈”,且關聯的內臟是“心”,而不是“肺”,至《足臂十一脈》《陰陽十一脈》甲本仍只有臂太陰脈與心關聯。後來上肢的經脈從“臂陰脈” 一分為二、一分為三,但直到老官山“十二脈”文字,“臂太陰脈”“臂少陰脈”和“心主之脈”行至上肢近端,皆趨於腋,最後又都歸於“心”,仍表現出“一脈三歧”的特徵。手三陰脈真正成為3條平行、獨立之脈的構建,實際上是在《靈樞·經脈》 最後完成的〔6〕167-169。
順便說,如果“間別臂陰脈”此簡不歸在經脈簡而歸於針灸方類,則多半會被理解為一首帶有方解的灸方。其實為脈俞遠隔診療作用提供解釋正是構建經脈學說的初衷。
2.2足太陰之別
兩條別脈“間別足太陰脈”以及“間□足太陰”名同而實不同:
簡419:·間別大陰脈:出□繚婢(髀),出深貪,臍上痛,奏於心痛,山□癃,遺弱(溺),久(灸)大陰〔1〕65。(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間□足大陰:□□外廉,出脾下廉,上尻外廉,屬大陽(腸)〔8〕21。(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簡419原文“臍上痛奏於心痛山”所說系典型的“心疝”病症,老官山出土醫簡469簡曰“心山(疝)繞齊而痛”,傳世本《靈樞》《素問》也皆有類似論述。此簡提示:
與前陰相關聯的脈曾被稱作“太陰脈”(這時很可能還沒有“厥陰脈”的名稱),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可見類似的文字:
簡051:□溲溺凡十一病,啟卻,久解上踝三寸,必廉大陰之察病,有煩也死,毋治〔1〕257.(老官山出土漢簡)
頹……灸其大陰、大陽□□。令〔15〕。(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箕門,在魚腹上越筋間,動脈應手,陰市內,足太陰脈氣所發。主癃,遺溺,鼠鼷痛,小便難而白〔11〕184。(《黃帝明堂經》)
從051殘簡不難看出,“溲溺”等十一病歸屬於“大陰”脈,而不是“厥陰”脈。《五十二病方》治頹疝方下所載之灸方也是“灸大陰、大陽”,不見“厥陰”之名;《黃帝明堂經》所載之“箕門”,部位及主治皆與簡419所述之“間別大陰脈” 很相近,同樣也歸之於“足太陰脈氣所發”。這些很可能都是早期經脈“二陰二陽”命名法的遺存,而在馬王堆出土《足臂十一脈》《陰陽十一脈》,與前陰關聯的脈已明確定為“厥陰脈”,相應地在漢初倉公醫案中,氣疝、前陰病已經明確歸於“厥陰之動” ,治療也“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在《陰陽十一脈》厥陰之脈下記有“五病有而心煩死,勿治也”字樣;《足臂十一脈》足厥陰脈作“皆有此五病者,有煩心,死”,則提示051殘簡所說的“太陰”脈在這時已被貼上“厥陰”的標籤了。
至於另一簡所言“間□足大陰:□□外廉,出脾下廉,上尻外廉,屬大陽”,在傳世本《素問·繆刺》猶見這一分支古本的佚文: “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兩胂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為痏數,發針立已,左刺右,右刺左”〔9〕349。由於“尻外廉”已屬太陽脈分野,故簡文曰“屬大陽”正確無誤,整理小組釋作“大腸”,非是。
2.3足太陽之別
·足大陽脈,出肩胛下廉,繞胸屬乳下。 其病:肩胛下廉痛,胸衡肩〔1〕236。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此脈循行為起止兩點間的一脈相連; 病症為起止兩點處的痛症; 起點為脈之所“出”處,皆與前述之“間別臂陰脈”的特徵相同,所不同者,此脈病候前增有“其病”二字,使得文字層次更加清晰。 這一體例被後來的《足臂十一脈》所沿用。
在同墓出土的針灸木人上,足太陽脈借助於足少陽脈的介導而與足陽明脈關聯。 無獨有偶,傳承扁鵲醫學的《劉涓子鬼遺方》也有關於足太陽分支與足陽明脈關聯的記載:“腰太陽脈有腫,交脈屬於陽明,癰在頸”〔16〕。 足見背部足太陽脈與胸前陽明脈之間的關聯來自於實踐經驗的總結。 這類別脈存在的意義在於解釋臨床上發現的痛症前後相引的關聯規律,為前後配穴的“偶刺”法提供了理論支撐。 在《素問·舉痛論》對於“心與背相引而痛”這種痛症前後相引的現象進行了專門探討,給出了如下的解釋:“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9〕220,與老官山文字同樣都以脈的聯系解釋, 有所不同的是老官山文字採用足太陽脈從背部繞行胸前的聯繫方式,而《素問》採用的是從背俞至心的直接聯系。
在經脈文字定型化的過程中,這些脈既沒有以分支或絡脈的形式與“十二脈”形成互補關係的理論假說,又沒有為此另立新說,從而使得經脈理論與臨床實踐之間出現了“斷裂”。
老官山“別脈”簡保存了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脈”的文字,其中應當存留有“人體三陰三陽縱向分佈法則”確立之前的文字,這些早期文字描述的“脈”,與經過規範化處理後的經脈循行,會有不同的循行模式,例如陰脈有可能行於胸腹之錶, 也可能上行於頭面。 期待老官山醫簡的完整公開帶給我們更多的新發現。
3診脈法
診脈與經脈學說的構建與演變密切相關,故《靈樞·九針十二原》強調“凡將用針,必先診脈”〔7〕3。 從出土文獻到傳世文獻,經脈文獻中都有診脈內容,馬王堆、張家山、老官山出土經脈文獻,關於診脈,既可見某些經脈下的具體論述,又有歸納為一般性的專篇論述。 現時已經公開的老官山出土漢簡中,有關診脈的內容還很有限,難以進行系統考察分析,以下僅就老官山與馬王堆、張家山出土文獻共有的一段診脈法文字加以探討。
·相脈之道,左□□□□□案之,右手直踝而簞之。 它脈盈,此獨虛,則主病。 它脈滑,此獨澀,則主病。 它脈靜,此獨動,則主病〔3〕126。 (張家山漢簡《脈書》)
相脈〔之道〕,左□□□走而案之,右〔手直踝而簞之。 它脈〕盈,此獨虛,則主病。 它脈汩,此獨□,則主〔病〕。 它脈〔靜,此獨動,則主病〕〔3〕127。 (馬王堆帛書《脈法》)
簡623:相脈之過,左手直果五寸而案之,右手直果而單之。 應手如三舂,死。 不至如食間,死。 地脈盈此獨〔虛,則主病〕〔1〕74(老官山出土漢簡)
以上診脈法在傳世文獻《素問·三部九候論》中有完整的論述,相應文字又見於編號P3287的敦煌卷子,可據以補正《素問》文字的缺訛。 根據《素問》所載的完整文字,可知張家山《脈書》的診脈法實為兩種不同的診法,一為“决死生”診法; 一為“知病之所在”的三部九候診法,句首有脫簡,故其正確的斷句應如下分作兩段:
·相脈之道,左□□□□□案之,右手直踝而簞之。
〔察上下左右之脈〕,它脈盈,此獨虛,則主病。 它脈滑,此獨澀,則主病。 它脈靜,此獨動,則主病。
老官山文字所述也是兩種診脈法,亦有脫文,正確文字及斷句應如下作:
相脈之過,左手直果五寸而案之,右手直果而單之。
〔上下左右之脈〕應手如三舂,死; 不至如食間,死。
〔察上下左右之脈〕,地脈盈,此獨〔虛,則主病〕……
補正文字,理清段落間的關係,以往對出土文獻解讀中的困惑大多冰釋,前兩段說的是“决死生”診法,後一段是說診“有過之脈”以知病之所在。 可見老官山漢簡將原文本“相脈之道”改作“相脈之過”,一字之錯而大失原文本義。
對於上述共見於馬王堆、張家山、老官山的“决死生”診脈法,學者的解讀有很大的分歧:或說是診動脈,或說是彈踝診法,或說是彈擊神經。 其實只要在人體實際操作幾遍就很清楚古人說的是什麼,如果觀察的是動脈和神經,那麼不應當受體位的影響或影響很小,而事實上當你把下肢平放地上或診床上,再做同樣的操作時“應動”就變得很微弱,不仔細體會甚至很難察覺; 當你平躺再抬腿90°時,“應動”便完全消失。 通過這個簡單的實驗便可斷定,古人觀察的是靜脈血的回流狀態。
具體診法如下:病人站立比特或坐位,醫者左手2–4指平放於病人內踝上方,用右手單指(如示指)或二三指(如示指、中指、環指)輕叩踝前顯露的絡脈(大隱靜脈),體會左手指下的脈應動狀態:如果應指的力度和緩、速度適中為正常; 如果應指不及踝上五寸,或完全不應者,則為死征。 可見,這是一種“决死生”的特殊診法,在傳世本《靈樞》《素問》還可見明確的應用實例。
4討論
如果僅僅論證了老官山出土脈書簡與扁鵲醫學密切相關,還不足以說明出土的其他醫簡與扁鵲醫學的關係,只有找到連接脈書簡與其他針灸簡,以及針灸木人之間的一個個“鏈環”,才能為老官山出土漢簡的定性提供完整的證據鏈。
4.1老官山脈書簡與其他針灸簡及針灸木人的關聯
在“十二脈”文字中,足太陽脈有一特徵性的改變——從膕窩部郤中分出一支上行至肛,而在同墓出土的針灸木人上,足太陽脈內側線恰好也有一分支從郤中至肛,此乃這具針灸木人明確受到了老官山“十二脈”影響的强有力證據。
《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曰:“心氣者赤,肺氣者白,肝氣者青,胃氣者黃,腎氣者黑,故以五藏之氣□”,而同墓出土的針灸木人五臟之俞的選定及其排列次序與此完全相同,並與《扁鵲針灸經》佚文相合,都深深打上了扁鵲針灸的烙印〔17〕。 這些反映扁鵲醫學特徵的醫簡與同墓出土的其他醫簡,特別是與體現扁鵲針灸典型特徵《針方》的關係,還有待全部出土漢簡釋文公開後進一步考察。 有關老官山出土《針方》簡的解讀,擬另撰專篇,本文不展開討論。
現已公開的部分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中,能辨識出的扁鵲醫籍以針灸文獻為多,一方面提示針灸學在扁鵲醫學佔有重要地位,有較多的著述傳世; 另一方面也因為對扁鵲醫學的“指紋”,現時選取到的也以針灸學為多,故比較方便辨認。 墓主人能收集到這些扁鵲醫籍,一方面與其興趣愛好有關; 另一方面也說明扁鵲醫籍當時還流行,比較容易收集到。
需要指出的是,老官山出土的扁鵲醫籍表現出不同時期扁鵲醫學的不同特徵,保留著扁鵲醫學之樹不同年代的“年輪”,例如《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曰:“心出臂少陰,肺出臂太陰,腎出骭少陰,胃出足太陰”〔1〕71,其中“心出臂少陰”“腎出骭少陰” “胃出足太陰”三者在“十二脈”文字中皆可找到明確的對應文字,而“肺出臂太陰”未見明確的對應文字,但在新添加的“心主之脈”循行文字中已見端倪——“入匈(胸),循匈(胸)裏,上加大陰,上循□嚨,下系心”〔8〕14,暗示“胸裏” 乃臂太陰脈之分野,從而埋下了該脈與內臟的關係從“心”轉變為“肺”的伏筆,至《靈樞·邪客》的“入腋下,內屈走肺”〔7〕127則完成了這一轉變。
另需指出的是,在辨識老官山出土醫簡與扁鵲醫籍的關係時,不能以是否見有“敝昔曰”字樣作為鑒定的主要或唯一依據,哪怕“敝昔”二字確定無疑為“扁鵲”二字的假借字。因為書中出現“扁鵲曰”字樣可以有2種不同的情况:其一,“扁鵲曰” 三字乃扁鵲書中原有文字,後人抄錄時依舊照抄;其二,扁鵲原書中沒有“扁鵲曰”字樣,後人在引用其文字時在句首冠以“扁鵲曰”字樣以示文獻出處。但古籍引文不用引號,這種情形很可能是全書或全篇只有文前冠以“扁鵲曰” 的文字出自扁鵲醫籍,其他文字或引自他書,或出自編者之筆,皆與扁鵲醫籍無關。此外還有另一種情形,扁鵲原書就無“扁鵲曰”字樣,後人抄錄時也依舊抄錄,這時就不能因為文中沒有“扁鵲曰” 之字而否定其出自扁鵲醫籍之實,更不能因為在這樣的抄本中或出現幾處“黃帝曰”文字而輕率將其定為“黃帝醫籍”——全書可能只有標注“黃帝曰” 的文句出自黃帝書,其他文字則皆抄自扁鵲醫籍。由於現時老官山出土醫簡釋文尚未全部公開,其文字抄寫管道有幾種?引文標注管道有幾種?還無法詳細考察。
4.2散脈·經脈·別脈
老官山出土漢簡脈書雖然晚於馬王堆脈書和張家山《脈書》,卻保存了不同時期的文字,包括比馬王堆和張家山出土經脈文獻更古老的文字,以及同源文獻的不同版本(抄本),為考察經脈學說的形成和演變軌跡提供了一個個關鍵“路標”。
最簡單聯系之脈的形態猶見於老官山脈書“間別”脈:脈之所“出”之處乃脈之起點,所診、所治之遠隔部位即脈之止點,脈之病候即起止部位處的病症,且常常表現為相關部位的痛症。這時期的“脈”表現為“一脈一俞”的特徵,且借用《素問》“散脈” 一詞以名之,以下試以“脥脈”為例粗略重播從“散脈”到“經脈”的演變軌跡:
·間別臂陰脈,出脥,凑心。脥痛,心痛,久(灸)臂陰〔1〕238。(老官山出土漢簡)
臂太陰脈:循筋上廉,以奏臑內,出腋內廉,之心。其病:心痛,心煩而噫。諸病此物者,皆久(灸)臂泰陰脈〔2〕6。(《足臂十一脈》)。
“臂陰脈”的循行特點表現為以脈“出”之處“脥”與該脈所診療病症的部位“心”兩點之間的一脈相連,即“兩點一線”的脈行模式。這樣孤立、零散的脈發現再多,也只能解釋一個個具體的臨床經驗,而且臨床上發現多少個具有遠隔診療作用的“俞” ,便需要構建多少條這樣的脈來解釋其遠隔診療作用,無法構建出結構簡單而解釋力强的理論假說。直到在這一條條互不相關的“散脈”中發現彼此間的聯系,並閃現出這樣的思想火花——將相關聯的“散脈”連成一條脈,將多個“散脈” 的診療病症加以綜合。在老官山出土漢簡9條“間別”脈中“間別太陰”“間別少陰”等脈循行路徑所“出” 之處已見有多點,病候也相應更加豐富,標誌著在新思路引導下聯系之脈的突破性發展,而集中反映這一時期發展成果並進行規範化理論構建的代表作乃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
《足臂十一脈》所載之“臂太陰脈”,從循行上只比“臂陰脈”多出一點——“循筋上廉”,《陰陽十一脈》對這一點有更詳細的描述“在於手掌中,出臂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據此可確認此處相當於腕上掌側“太淵”脈處,依例《足臂十一脈》 原文當作“出筋上廉”,然而兩條手陰脈起點皆作“循”而不用“出”字;從病候上看,較之“臂陰脈”也多出“心煩而噫”症,而《黃帝明堂經》載“太淵”主治症中恰好有“心痛”“煩心”“噦噫”症,明顯可見《足臂十一脈》臂太陰脈病候從原先的“脥脈” 和後出的“太淵脈”主治綜合而來的痕迹。
雖然這時的“臂太陰脈”,僅僅在循行上多出一點,病候上多出一症,卻完成了經脈學說構建歷程上的一次根本轉折。當多個散脈被綜合為一條脈之後,則表現出以最少的“脈”承載最多的經驗事實的特徵,因而在臨床上獲得更廣泛的應用。而當古人基於 “天上人相應”的理念,將脈之常數確立“十一”“十二”時,這些已經在臨床上獲得更廣泛應用的綜合之“脈”自然優先入選,是謂“經脈”。這以後“脈”的發展就主要體現於“十二經脈”內部,而沒有進入“經脈”系的脈便停止發展,並漸漸淘汰、消亡。
及至漢初,老官山《脈書》中又另設“別脈”類以存放當時已經被邊緣化、尚未消亡、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脈的文字。
被存放於“別脈”類中的各類“脈”有3種歸宿:
其一,以經脈之“別”的形式出現,例如在《內經》猶可見,足三焦脈為足太陽之別; 陰蹺脈為足少陰之別等; 在老官山出土的針灸木人出現了十三道白脈,似乎提供了一個反例。 經仔細考察判定,其中行於下肢背側、腰背部、後頭部的兩道脈同屬於“足太陽之脈”,即木人刻畫的十三道白線實為“十二脈”的體表循行線。 這種將人體背面並行兩道脈同歸於足太陽脈的思路還直接影響了傳世本《靈樞·經別》,所述足太陽之正明言“其一道下尻五寸”〔7〕39,清楚地表明:這時,足太陽脈在膕之上的循行已經有兩道; 同時《靈樞·經筋》“足太陽之筋”也為兩道,說明該篇編者參照的“十二脈”文字之“足太陽之脈”也是兩道脈。 足見在確立了經脈“十二”常數之後,“十二脈”之外的脈只能以“別脈”的形式附屬於十二脈,而不能超越“十二”之數。
其二,以“俞”的形式出現,這也是“別脈”獲得新生的最主要的捷徑。 例如《黃帝明堂經》所載之“俠白”則記錄了從“臂陰脈”從“脈”到“俞”的演變,且猶見其從脈而來的明顯痕迹——“手太陰別”。
其三,在“別脈”這一大筐之中繼續以“脈”的形式存在,靜候經脈理論框架的調整而獲得不期而遇的“新生”。 例如當經脈之數從“十二”(左右則為“二十四”)調整為“二十八”時,任脈、督脈以及蹺脈之一便升格為“經脈”; 而當經脈之數從“十二”變為“二十七氣”時,則當時尚未被丟棄的“別脈”則被統一“著裝”形成“十五別”(又稱“十五絡”),與“十二經脈”共成“二十七氣”,而有“經絡”之稱。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靈樞·經脈》十五“別”與老官山《脈書》十“間別”,皆曰“別”,但實質內容並不相同:《靈樞》十五“別”脈又稱“十五絡脈”,雖然這些絡脈的原型也出自非常古老的文字——有些甚至與老官山“間別”脈中最古老的文字一樣古老, 但已按統一的理論框架進行了改編,其循行文字中已經明確了與經脈循行的聯系,作為經脈的分支而成為了經脈的一部分,並與十二經脈共同構成“二十七氣”之數,因而絡脈之數是固定的,不多不少定為“十五”; 而老官山“間別”是沒有進入“十二脈”框架的所有處於不同發展階段“脈”的輯錄,沒有以此為素材進行再創造,在循行上沒有與“十二脈”建立關聯,其數量也沒有任何限定。 從同墓出土的《針方》已經載有至少4個確定的“落俞”來看,當時已有“落脈”的概念,而且應當有論述“落脈”的專篇。 雖然從現時已經公開的老官山醫簡的釋文中已見有落脈診病的醫簡,但還未見專門論記述“落脈”循行和病候的醫簡,其與老官山“間別”脈以及《靈樞》“絡脈”的關係尚有待考察。
4.3《脈書》的傳承管道與演變軌跡
在老官山漢墓之前的出土文獻以“脈書”為書名者見於張家山出土漢簡《脈書》,其基本構成包括:病候(六十多種病名及症狀)、經脈(十一脈的循行與病候)、診脈(診脈法,包括脈死候)3個部分。
老官山出土漢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簡(簡361–628)恰好也由這三部分構成,也當出自《脈書》的一種傳本。 馬王堆帛書被專家定名為《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候》的3種書,實際相當於張家山《脈書》的第二、第三部分,應視為《脈書》的一種早期傳本。
3處漢墓出土的3部“脈書”的共通部分為“經脈”和“診脈”,《脈書》的這一基本構成和編纂體例實際上正反映了經脈學說與脈診的密切相關,迄今讀到的經脈文字,不論是出土文獻還是傳世文獻,都包括了兩部分:“循行”和“病候”。 直到十二經脈的最後一個版本——《靈樞·經脈》中,其“病候”文字猶可見明顯的從脈候脫胎而來的痕迹。 《靈樞》第一篇所說“凡將用針,必先診脈”〔7〕3,正是對經脈與脈診緊密聯系的一種表達。
從這一角度讀傳承扁鵲脈書的《脈經》,對該書前六卷同樣是“診脈”和“經脈”的基本構成也就不難理解了。
再看《靈樞·經脈》的基本構成:“十二脈”; “診脈法”(包括“脈死候”); “十五別脈”,以往很難理解這些今天看來明顯屬於不同主題的內容怎能同時被輯於“經脈”專篇,現在知道老官山“脈書”的第二、三部分同樣包括“十二脈”“診脈法”和“別脈”三部分,可見《靈樞·經脈》傳承了老官山“脈書”的結構與內容, 因而也可以將其視為老官山“脈書”的一種傳本。
通過馬王堆、張家山、老官山三座西漢墓藏出土的脈書簡的比對,可以推知在西漢早期,《脈書》除了像張家山出土的單書形式外,還有一種與《足臂十一脈》合抄的“合抄本”(相當小叢書的性質)流傳。 這種合抄本除了見於馬王堆出土帛書外,老官山出土漢簡“十二脈”編者所引用的《足臂十一脈》很可能也是一種與《脈書》合抄的合抄本,因為張家山出土《脈書》“十一脈”文字已經具有明顯的“定本”特徵,在這一背景下, 作為在學術層面上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足臂十一脈》,再以單行本流傳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說老官山、張家山、馬王堆出土的都是《脈書》,為何老官山出土漢簡“脈書”在具體內容上與前面兩次出土文獻有較大出入呢? 在劉向校書確立定本前,漢以前古籍之所以出入很大,與抄者的“再創作”有關,在那個年代除外法律、檔案文字外,大概很少有純粹的抄寫者,特別是私家藏書,抄者無“定本”意識,在抄寫的過程中出於某種需要或多或少會進行“再加工”。 傅榮賢〔18〕在系統研究出土簡帛文獻後提出了“抄寫即創造”的觀點:作為簡帛文獻最根本特徵的傳抄本,其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抄本與原本之間以及同一原本的不同抄本之間沒有完全相同的本子。 抄者傳抄什麼,常常受抄者所處的時代,及墓主個人的學術取向和興趣愛好的影響。 囙此“同墓複本之間沒有完全等同的文字”; “非同墓複本之間更沒有完全等同的文字”。
具體到老官山“脈書”,第一部分“病候”約205枚簡,整理小組依據其不同的體例定為《諸病一》和《諸病二》兩種書。 筆者發現已公開的《諸病二》釋文體例與《史記·扁鵲倉公傳》倉公所論病症體例完全相同,則這部分病症簡當抄自扁鵲《脈書》,其他簡或另有所出; 第二部分“十二脈”已確認系出自兩種書——《陰陽十一脈》和《足臂十一脈》,其抄寫管道為“改編合抄”; 第三部分現時公開的釋文很有限,還不好考察出處。 採用這樣抄錄管道改編而成的“脈書”,其“純度”自然明顯不如抄錄規範、體例嚴謹的張家山《脈書》,甚至也不及更早的馬王堆《脈書》。
也正由於這個原因,可以將老官山出土漢簡361–628部分稱作“脈書”,卻不宜稱作“扁鵲脈書”。
老官山《脈書》的改編也標誌著各家學說綜合的開始,甚至在更早的《陰陽十一脈》已經開始了,而規模最大的一次“大一統”理論綜合的成果集中體現在傳世本《靈樞》《素問》。
將現已公開釋文較多的老官山《脈書》“十二脈”文字與張家山《脈書》、馬王堆《脈書》“十一脈”文字對照後發現:張家山《脈書》“十一脈”體例最嚴謹、最合理,抄寫也最規範,顯然是古籍規範化整理的產物,帶有明顯的“定本”特徵。 而老官山“十二脈”體例最不嚴謹,且不時見有抄者剪輯文字時低水準的“再創造”。 然而也正因為沒有經過“規範化”的整理,那些文字定型化之前的“不規範”文本才得以在老官山《脈書》中原貌存留,單從現時公開的部分老官山《脈書》簡釋文來看,至少可以分辨出4種不同時期的經脈文字:其一,“十二脈”; 其二,被摻入《馬醫書》的8枚經脈文字殘簡; 其三,9條“間別”之脈; 其四,3條“別脈”。 甚至同一篇中也可見不同時期抄本的輯錄,例如9條“間別”脈明顯可見出自不同時期不同發展階段的“脈”的文字。 這些不同時期不同經脈文獻的抄本使得考察“十二脈”定本之前版本源流成為可能,試以手太陰脈為例顯示不同時期“經脈”版本的基本特徵如下:
版本1.0:臂陰脈,出脥,凑心。 脥痛,心痛,久(灸)臂陰〔1〕238。 (老官山漢簡“間別”脈)
版本2.0-1:臂泰陰脈:循筋上廉,以凑臑內,出腋內廉,之心。 其病:心痛,心煩而噫。 諸病此物者,皆久臂太陰脈〔2〕6。 (馬王堆帛書《足臂十一脈》)
版本2.0-2:臂钜陰脈:在於手掌中,出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內陰,入心中。 是動則病:心滂滂如痛,缺盆痛,甚則交兩手而戰。 (佚名書“十一脈”)
版本3.0:臂钜陰脈,在於手掌中,出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臂內陰,入心中。 是動則病:心滂滂如痛,缺盆痛,甚則交兩手而戰。 其所產病:胸痛,脘痛,心痛,四末痛,瘕,為五病〔2〕12。 (《陰陽十一脈》)
版本3.1:辟(臂)大陰脈,系手掌中,循辟(臂)內陰兩骨之間,上骨下廉,〔筋之上〕,出辟(臂)內陰,至亦(腋),入心〔8〕13。 (老官山漢簡“十二脈”)
版本4.0: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手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出)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為臂厥。 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 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 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7〕30。 (《靈樞·經脈》)
版本2.0-2的原本尚未發現,書名不詳。 但此本的存在是生成版本3.0的先決條件,而且據筆者考察,版本3.0完整繼承了版本2.0-2的理論框架和編纂體例,也就是說通過版本2.0-2綜合版本2.0-1而形成版本3.0。 該版本,特別是張家山出土的《脈書》版體例規範、合理,抄錄嚴謹,是對早期諸家“十一脈”一次較系統的規範化綜合,帶有明顯的“定本”特徵。 與其他漢以前古籍流傳規律一樣,“定本”一出便廣為流傳,而其他早期傳本便漸漸失傳。
《陰陽十一脈》先後出土3種抄本,傳世文獻《靈樞·經脈》也以此傳本為主本編定,足見其流傳之廣。 然而似乎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足臂十一脈》某一抄本因與《脈書》合抄而得以保存下來,故老官山《脈書》編者得見,《靈樞》編者也得見——儘管所見可能非同一傳本(抄本)。
在版本4.0,六條陽脈皆入行於體內,十二脈與十二內臟建立了明確的對應關聯,但最根本的變化在於十二脈依次連成一首尾相接的“連環”,十二脈循行方向一半自下而上,一半自上而上,十二脈的排列次序也被嚴格規定。
在4個版本之間還存在著若干個過渡版本,例如在版本1.0與版本2.0-1之間,曾出現在1.0版本病候前加有“其病”二字者; 版本3.0與版本4.0之間也有若干個過渡版本,老官山“十二脈”是其中之一,且稱作“3.1版”,實為“節外生枝”的一個文字。 詳見下文“十二脈”編輯得失。
4.4“十二脈”編輯得失
老官山“十二脈”編者的最大貢獻在於在《陰陽十一脈》《足臂十一脈》“十一脈”基礎上,新增一條“心主之脈”,使“經脈”之數定為“十二”。 沒有這一鋪墊和過渡,就不可能出現後來《靈樞·經脈》“如環無端”的經脈流注新說的構建。 從老官山《脈書》“十二脈”文字編者對原文本的理解和改編所體現出的學識來看,新增的“心主之脈”不大可能是該編者從無到有的“創造”,很可能原文本已經存在,他直接抄錄(或略加改編); 或者已有記述此脈的文字,只是還沒有“心主之脈”的名稱,他抄錄時將脈名厘定為“心主之脈”。
關於“十二脈”文字的改編失誤,已在前面的文字考察時具體指出,可歸納為以下幾類:第一,不明原文本之義而誤改原文; 第二,脈名格式不統一; 第三,病候抄錄了《陰陽十一脈》丙本的“是動病”和“所產病”中的病症,但在手太陽脈以“所生病”統之,而在其餘十一脈則以“其病”二字統之。 病症排列次序有按《陰陽十一脈》作自上而下排列的,也有按《足臂十一脈》自下而上排列的,體例既不統一,更不合理; 第四,新增病症前既無明顯的標識,也沒有置於固定的位置。
出現這些失誤,與編者的學術傾向、愛好、抄錄目的等因素皆有關,而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抄寫者(或“改編者”)未明《足臂十一脈》與《陰陽十一脈》二者的關係,以及二者不同的體例。
如前所述,《陰陽十一脈》系將一種佚名書“十一脈”文字與《足臂十一脈》綜合而成,也就是說,《足臂十一脈》的內容已被吸納在《陰陽十一脈》這一版本中了,不能用已經用過的素材再來一次綜合。 如果老官山“十二脈”編者擁有的《足臂十一脈》版本比《陰陽十一脈》當時採用的版本要好,可以用這個更好的版本來糾正《陰陽十一脈》當時綜合中的錯誤,或彌補其缺漏之處; 如果老官山“十二脈”編者想採用不同的理論框架和體例重新綜合,那麼他首先需要理解並分清生成《陰陽十一脈》這一合成本的兩個子本的不同體例和背景:第一,當一條脈上所“出”之點不在同一方向時,《足臂十一脈》是用主幹連接同一方向的各點, 而用分支去連接偏離主方向的點; 佚名書“十一脈”則用同一條脈,以“變向折返”管道連接各點。 第二,關於病候,《足臂十一脈》所述乃經脈循行部位上的痹、寒、熱病症(病症部位與脈所“出”之點對應); 而佚名書“十一脈”多系一組有內在聯系的症候。 二者是基於兩種不同的診脈法所總結的兩類不同性質的病候。 第三,關於病候的排列與標注,《足臂十一脈》是自下而上排列,病症前冠以“其病”二字; 佚名書“十一脈”的病候皆自上而下排列,病症前冠以“是動則病”字樣。 《陰陽十一脈》是完全按照佚名書“十一脈”的體例綜合了《足臂十一脈》的“十一脈”。 倉公醫案所引厥陰脈、陽明脈的病候悉見於張家山《脈書》相關脈的“是動則病”,說明倉公所受之扁鵲《脈書》經脈文字或者是《陰陽十一脈》之前的版本(版本2.0-2),或者是《陰陽十一脈》的某一傳本。 同時也提示,《陰陽十一脈》的編者應是扁鵲醫學的傳人,否則不大可能完全以反映扁鵲醫學特徵的“十一脈”理論框架和體例,完成這次“十一脈”的理論綜合。 如今,老官山“十二脈”編者卻明顯表現出對扁鵲經脈文獻的生疏或疏遠。
如果說老官山“十二脈”編者因為學術傾向的不同,想換一種方法重新綜合,那也應當首先將《陰陽十一脈》中綜合後的文字進行剝離(難度極大),然後再用《足臂十一脈》的體例和框架進行綜合。 而不能有的脈採用《足臂十一脈》的模式,有的脈又沿用《陰陽十一脈》舊有的模式; 更不能在同一條脈中一部分用《足臂十一脈》模式,另一部分用《陰陽十一脈》模式。 例如在足太陽脈,循行路徑的表述,下肢部採用《足臂十一脈》模式,頭面部又用《陰陽十一脈》模式; 病症的排列次序,又採用《陰陽十一脈》“自上而下”排列,病症末又新增6個病症。 在《陰陽十一脈》丙本,凡新增病症前皆冠以“及”字,不與原文本病症相混,而“十二脈”文字新增病症前既無“及”,也沒有任何其他標識。 所有這些失誤都說明“十二脈”編者既不明《足臂十一脈》《陰陽十一脈》二者的關係,也不明二者不同的體例,更沒有意識到在同一條脈中採用二種不同的體例使之成為無法理解的“怪物”。 因為採用“分支”模式的目的正在於避免循行路線出現複雜的“折返”,如此同一條脈中一前一後採用兩種不同的連接模式,從而使得新編文字的循行路線變得不倫不類(如果用圖形表現出來看得更加明顯),是一種無法理喻,無法容忍的錯誤。 其他脈中的嚴重失誤也多由此而生。 從總體上看,“十二脈”文字改編並不成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次“倒退”。 也許改編者原本只是方便自用,不為傳播,無意在張家山《脈書》版“十一脈”的基礎上,創新體例,完善內容,編成一個新的“定本”。
至於老官山“十二脈”編者是否還改編了同墓出土的其他醫簡,以及改編的管道是否與“十二脈”文字的處理管道相同,僅從現時公開的數量有限的醫簡釋文還難以判定。
5結語
老官山出土醫簡中361–628簡,簡的規格相同,體例一致,其基本構成、體例皆與張家山《脈書》相同,應定為同一部書,書名可題作“老官山《脈書》”,但不宜稱作“扁鵲脈書”。 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這部“脈書”已經參照了扁鵲醫籍之外的文獻進行了改編,可視為後來《黃帝內經》編者所完成的“大一統”醫學綜合的前奏。
老官山《脈書》中的“十二脈”文字所依據的底本為張家山漢簡《脈書》本《陰陽十一脈》(“丙本”)和《足臂十一脈》,編纂管道系兩個本子的合抄改編。 對原文本實質性的改編,在經脈循行方面,足太陽脈新增了一條從膕窩至肛門的分支; 在病候方面,綜合《陰陽十一脈》分屬於“是動則病”和“其所產病”的兩類病症,以“其病”二字統之,另增補有少量新的病症; 在經脈數量上,較原本厘定了一條新脈“心主之脈”。 由於“十二脈”編者不明《足臂十一脈》與《陰陽十一脈》的關係以及二者不同的體例,在改編過程中出現不少嚴重的失誤。
老官山《脈書》雖然晚於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的傳本,但卻保存了更早期的經脈文獻,特別是反映了“經脈”形成之前“脈”的早期特徵。 該書在完成“十二脈”的厘定之後,將當時尚存的不同時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其他脈皆歸屬於“別脈”類下,基於這些早期文字可推知,經脈學說在《靈樞·經脈》完成“十二經脈”定型化之前,至少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並出現了反映各個發展階段的經脈文字; 經脈的命名在採用“三陰三陽”命名法之前,還經歷過“二陰二陽”、“一陰一陽”命名法,同時提示“三陰三陽”命名法首先在足六脈應用,之後再類推至手六脈。
老官山《脈書》不僅是已知“十二脈”文字的最早版本,而且還是“經脈”與“別脈”明確分類的最早設立。 這一分類法對後來的《靈樞·經脈》產生了直接影響,該篇由“十二經脈”、“診脈法”和“十五別”三部分構成,其編纂思路、體例與老官山《脈書》如出一轍。
老官山出土的脈書簡及《逆順五色脈藏驗精神》,與同墓出土的、帶有鮮明扁鵲醫學特徵的針灸木人,存在著密切的內在聯系。 由此可知,老官山出土的醫簡至少有一部分為扁鵲醫籍,或據扁鵲醫籍改編。
參考文獻
[1]梁繁榮,王毅.揭秘敝昔遺書與漆人——老官山漢墓醫學文物文獻初識[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
[2]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4[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3]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4]謝濤,武家璧,索德浩,等.成都市天回鎮老官山漢墓[J].考古,2014,(7):64.
[5]田煒.論出土秦和西漢早期文獻中的“生”和“產”[J].中國語文,2016(2):202-210.
[6]黃龍祥.經脈理論還原與重構大綱[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6.
[7]靈樞經[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
[8]邱科.老官山漢墓經穴雲髹漆人像六陰經循行特點研究[D].成都:成都中醫藥大學,2016.
[9]王冰.黃帝內經素問[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79.
[10]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1: 105.
[11]黃龍祥.黃帝明堂經輯校[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87.
[1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3]丁度.集韻[M].北京:中國書店,1983: 1621.
[14]陳偉主編.裡耶秦簡牘校釋第1卷[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294.
[1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82.
[16]丹波康賴.醫心方[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333.
[17]黃龍祥.老官山出土西漢針灸木人考[J].中華醫史雜誌,2017,47(3):131-144.
[18]傅榮賢.出土簡帛與中國早期藏書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 276-281.
(收稿日期:2017-07-31,編輯:王曉紅)
作者:黃龍祥
文源:《中國針灸》雜誌